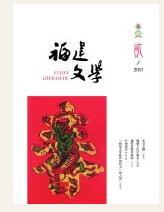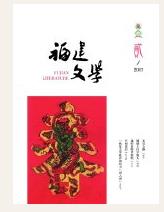
“客家乡土侠义小说”《汀江往事》(选二)
发表于《福建文学》2017年第2期
练建安
“天下水皆东,唯汀独南。”八百里汀江蜿蜒飘过闽粤大地,其间诸多风物掌故,似迷雾幻影,神秘莫测。沿江行走多日,采风及感悟得传奇若干,辑为《汀水谣》《鄞江谣》《迷云》《风水诀》。此为续集,一脉相承,追溯久远往事。题为:汀江往事。野人献曝,君子高人一哂。
枫树崟
您或许也有过这样的体验,一个月夜,您驱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山川原野在月色下朦朦胧胧,如梦如幻。
此刻,我在闽赣高速公路的一个休息区,遥望那若有若无的山脊线,山上阴翳的原始森林不见了。我的心中有许多感概,我想起了天地一瞬,人生如梦。是的,我想起了传说中的山都木客。
古书记载,闽赣边的枫松大树上,生活着一群山都木客,他们是一群小巧玲珑的人,“闻其声不见其人”,他们能歌善舞、豪放善饮。曾经有人在险峻的山崖听到过木客的歌唱,“酒尽君莫沽,壶倾我当发。城市多嚣尘,还山弄明月。”歌声美妙动听,隐隐的还有些忧伤,飘渺远去。
山都木客的消失,在历史上是一个悬案,人言人殊。
山都木客有记载的最后一次现身,是在一个汀江集镇的圩场上。目击者说,闪入人群不见了踪影。
记载者为练宝昌,邑廪生,曾为武邑知县幕僚,掌书案。新修族谱时,我在未刊稿《耕读斋剩笔》看到这一记载。
故里相传,武邑唐知县未发迹时,系江湖郎中,一日行走山路,在枫树崟救助了一位金毛披肩猴形低矮的折臂哑巴。哑巴频频回首,嗷嗷入林。
一溪远汇三溪水,千嶂深围四面城。此为闽赣边汀州。
入城,行至水东门,唐郎中走进河田米粉铺,要来一大碗,搭配一碟五香干,埋头呼呼大吃。临桌有位老者,瞄了瞄唐郎中的虎撑子。这物件是郎中行走江湖的白铜摇铃,有些年头了。老者好似自言自语:“知府高堂欠安,针药无效,杏林岂无人乎?”唐郎中抬头,老者已经走出了铺子。
夜晚大雨。临江客栈屋檐,水滴似断珠,嗒嗒作响。唐郎中酒碗在手,注目一只飞蛾环绕灯光旋转,自叹读书落魄,算命医药。忽闻瓦屋顶上有异常动静,刚起身,倏忽有块物件掉落在桌案上。推窗,但见空阔江面,烟雨茫茫。返回,挑亮油灯,此物竹叶重重包裹,打开细看,竟是一柄黑青灵芝。
此乃神品,极罕见。《神农本草经》云:“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
唐郎中毛遂自荐,治愈了知府高堂的怪疾。论功行赏,唐郎中啥也不要。恰逢知府统兵荡平悬绳峰山寇,遂以讨贼先锋冒名保荐,朝廷叙功任命唐文福为武邑知县。
福建巡抚听闻灵芝神效,指名向汀州知府索要。汀州知府限令唐知县克期上缴。
上哪儿去找呢?唐知县明白,他救助的哑巴,正是传说中形影神秘的山都木客。无奈,他再次来到了枫树崟,摆好三坛美酒,栖身茶亭。幕僚宝昌随从。俺太叔公文武兼修,系南少林高手。武邑县志有载。不赘。
一夜无事,唐知县倦缩在大棉袄里,迷迷糊糊竟睡着了。
太阳出来了,唐知县惊喜地发现,一柄黑青灵芝含露横卧在酒坛上。美酒原封不动。
如此这般,再三再四,灵芝总是神秘出现,只是越来越小了。
巡抚大人吹风说,近闻有冒名邀功者混迹要津,一经查实,必当严惩不贷。
好不容易才搞到一官半职,上了族谱,祠堂前还立了石桅杆,当官还真的当上了瘾。革职查办,岂非凤凰落毛不如鸡?唐知县很苦恼,就从“百味居”叫来几盘下酒菜,邀请宝昌陪同。喝者喝着,他就哭了。宝昌公能说什么呢?
八月廿二日,秋分。宜祭祀、结网、畋猎;忌开市、祈福、破土、造船。
唐知县又来到了枫树崟,带着“老三坛”。这次是冬至“酿对烧”,此物清冽香醇,滴酒挂碗。与以往不同的是,他还暗中布置了三十六名弓兵、捕快,统由“铁手神捕”带队,就近埋伏。
唐知县和幕僚宝昌走进了茶亭。他们颇为风雅,燃起松树明子,悠闲对弈。落子叮咚。他们留意着每一阵山风吹过。
唐知县接连出错,在屋内走了几个来回,又坐下。
“会来吗?”
“会来的。”
大半个夜晚,他们只有这两句简短的对话。
月影下,石坎上,静静地立着三口酒坛。
下弦月钻入云层。黑影闪过。
啪嗒,大网从天而降;哗啦啦,酒坛破碎。
唐知县跳将起来,顺手扯过松树明子,疾步赶到大网前。矮小山都浑身裹成了粽子,徒劳挣扎着,嘴含一柄小小的灵芝。他流下了眼泪。
唐知县也流泪了。
这滴眼泪,救了自己,也救了大伙的性命。
忽听林间沙沙有声,人影闪动。大事不好!唐知县念头甫转,就感觉到有硬物撞击胸口,昏黑倒地。
当他醒来时,已是次日天明。唐知县及其弓兵、捕快连同幕僚宝昌,皆为飞物所伤,片刻失去知觉。
山都,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铁手神捕”。
唐知县没有在官场上继续呆下去,“挂印封金”而去。幕僚宝昌随之退隐,在汀江流域象洞乡一个偏僻的山村亦耕亦读。
转眼到了清宣统年间,俺宝昌太叔公由玉树临风之年步入古稀。某日,他来到一山之隔的上杭中都镇墟场。年老嘴馋,他很想吃吃这里现做的热气腾腾的正宗“邱记鱼粄”。他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踽踽独行。这时,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几十年了,似乎没有任何改变。他努力往前挤,想打声招呼,说声抱歉。可是,那身影一闪而没。
太叔公郑重地记下了这一奇遇。《耕读斋剩笔》此刻就在我的手边。连城玉扣纸,大十六开本,一百七十六页,馆阁体楷书,每页八行,每行十九字,纸色泛黄。
窖藏
悦来客栈。这样的客栈到处都有不是?这一家,在汀江中游的大沽滩。
八百里汀江南流闽西粤东,出汀州,经武邑,过杭川百十里外,就到了大沽滩,下行不远,是一百年后将被淹没在水底的河头城,河头城之下,石市、茶阳镇之后,是大埔三河坝,汀江、梅江、梅潭河汇聚成了韩江。
大沽滩是杭川中都古镇水陆码头,人货辐辏。悦来的客栈规模最大,二进三十六间客房,楼高三层,青砖黑瓦,临江,风景好,推窗,但见白帆点点,往来穿梭。
客栈老东家是邱泰昌,木纲行商人,发了财,起了“九岽屋”,还从潮州人手里盘下了这家客栈。
老东家泰昌的满女嫁到武邑象洞墟去了,一年后生了“双巴卵”。做过周了,路近,泰昌和大婆带着幼儿鞋帽衣物去做客,归途经山子背,就遇到了一伙持刀蒙面人。危急关头,有壮汉挺身而出,扁担呼呼响,打跑了劫匪。
这人是挑担行长路的,姓练名金旺,早上挑米下广东石寨,无货上行,空肩归,路上就遇到了这档事。
泰昌问金旺一年赚多少银两?金旺就笑了,说挑担的,混碗饱饭就行啦。泰昌问他愿不愿意留在悦来客栈扫地,管吃管住,一年开二十两银子工钱。金旺想了想,就爽快地答应了。
山子背故事,悦来客栈无人知晓。金旺勤快,鸡啼起床,先把客栈门前的一条百十米长的青石板路扫得干干净净。半上昼,客人起床了,再扫院子内的。客栈的力气活,随叫随到。
店小二叫阿宝,是老东家的堂侄儿,是个“人来熟”,嘴杂,有事没事的,爱粘金旺。
金旺扫地,很有章法,时快时慢,或左或右,竹扫把在他手上,像是一根鹅毛似的。奇的是,地面坑洼,他扫把一次过,再挑剔的人,也找不出半点拉杂。
通常,金旺扫完地,洗漱,抓几个铜板,就到大碗茶楼去。他的早饭是三个大肉包,一壶茶。老东家说,你一年挣不了几个钱,爱喝茶,就算在俺名下。
早上,金旺又出去了。阿宝摸到大门角落,掂量掂量竹扫把,沉沉的,险些拿不动。摇摇,沙沙响,竹节里灌注了铁砂。阿宝有分寸,不说。
客栈按季发薪水。夜晚,阿宝拎了坛米酒来串门,找金旺喝酒。金旺拿出了一包五香牛肉干。大碗喝酒,喝得差不多了,阿宝凑近金旺说:“哥,俺和您说一事。”“你说。”“春香楼来了几个新鲜的,嘻嘻。”“嘭!”金旺将酒碗往桌上一蹲。“啊,啊,忘了关店门啦。”阿宝溜了。
转眼到了腊月十六,过年气氛浓了。老东家设晚宴,请来众伙计。这就是闽地习俗“尾牙宴”了。酒席上,鸡头正对着帐房先生,老东家又将一块鸡腿夹在他的碗里,说是辛苦了。帐房先生强颜欢笑。他明白,按规矩,他被解雇了。
次日晨,金旺刚抄起扫把,阿宝就粘了过来,悄声说:“帐房先生,昨夜就走了,说是短了银子。”金旺不搭理,阿宝一脸诡笑:“他,他是老板娘的表哥,表哥哦。”金旺盯了他一眼:“闲嘴咬鸡笼!”
老板娘是老东家的小妾,在潮州做生意时带回来的,叫银花,大婆说她是“狐狸精”。银花后来生了个带把的,起名文龙,上蒙馆了,平日里就和娘亲住在悦来客栈。
开春的一天,文龙半夜闹肚子痛。银花拍门,金旺二话不说,背起文龙飞奔“悬壶堂”。小华佗问诊施药,文龙当即就不喊痛了。小华佗捻着花白胡子说:“银花呀银花,幸亏你这伙计跑得快,迟几步,嘿嘿,就难说啰。”
老东家特地提了一坛全酿酒,送给金旺,说,金旺啊,好,好,俺不会看错人的。
悦来客栈人来人往的,被褥是一天一换。这就雇请了本地张二嫂洗晒打理。张二嫂人高马大,脾气也大,手脚却麻利。只要是晴天,日见她在井台边提水,洗洗涮涮的。一个上午,白净的被褥就挂满了整个庭院。
金旺扫地,一身臭汗的。换下褂子,自家去搓洗。张二嫂搭眼一瞄,装着没有瞧见,一句客气话也没有。
这天上午,阳光暖洋洋的。银花歪在柜台边嗑瓜子,扒拉着算盘,啪啪响。她眼尖,看到金旺端着满木盆衣物往井台边走去。
“金旺,你过来!”
“哎,叫俺?”
“过来。”
“哎。”
银花叫金旺把木盆放下,说,这些活,叫张二嫂干就是了,一个大男人,怎么好意思抢女人的生意呢?金旺脸红耳赤,不好还嘴。
汀江日夜流淌,日子就这么不急不慢地过去了。
金秋九月,客栈庭院的柿树结满了红艳艳的果子,落叶遍地。
昨日,入住了一位赣州客商。他招呼伙计抬入了十二箱重物。客房彻夜亮光,一大早,他们结账走人。
金旺晨起扫地,帮苦力搭了把手。客商咳嗽一声,伙计头目就推开了他。这个早上,金旺手脚慢了些,扫好地,差点错过了大碗茶楼的头笼包子。
夜晚,阿宝老辗转难眠,就起床摸到金旺的房门,轻敲,低叫,无人应答。竖耳听,没有动静,往日的如雷酣声呢?阿宝蹑手蹑足缩了回去。
一夜无话。
第二天,整个古镇都沸腾了。说是那个赣州客商不是客商,是当大官的,致仕回家,带了十二箱金银珠宝,一路小心翼翼,日宿夜行。不料,昨夜船过七里滩时,被打劫啦。汀州府捕快,全体出动搜捕。
洗漱毕,金旺请阿宝一同去大碗茶楼。阿宝很兴奋,一路上连蹦带跳、喋喋不休的。
大碗茶楼颇热闹。一壶茶二碟六个大肉包端上来了。阿宝举筷,左肩被拍了一下。抬头,就看见一个大汉,刀疤脸。他说,借一步说话。
阿宝随刀疤脸坐到另桌去了。
“这位小兄弟,寨背人么?”
“是的。”
“老父篾匠,老娘做媒婆。”
“是啊,咋啦?”
“家有小妹,送张家寨做童养媳啦?”
“咋啦?”
“没啥,随便聊聊。”
说完,刀疤脸也叫来一壶茶、三个大肉包子,不再理睬阿宝了。
阿宝嘟嘟囔囔回到金旺桌边。金旺头也不回,筷子指向大肉包子,说,趁热,趁热吃。
三天后,金旺来“九岽屋”找老东家,说是想回老家了,要辞职。老东家说,回家,随时都行。蔽号有啥事对不住你的吗?说说。没有,哦,工钱好商量哪。话说到这里,金旺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转眼到了重阳,当地客家习俗要尝新禾打糍粑。九日上午,庭院柿树下,洗净了石臼,端出了蒸糯米饭。金旺和阿宝一左一右挥动木杵,起起落落。同样一右一左搅动石臼中糯米饭的,是银花和张二嫂。
“嘭……嗒。”
“嘭……嗒。”
热气腾腾的糯米饭散发出诱人的清香。
“嘭……嗒。”
“嘭……嗒。”
热气腾腾的糯米饭在竹板的搅动下,袅袅嫩嫩,洁白如玉。
金旺扬起手臂时,一不留神,手背碰到了银花的胸部,春光乍泄。
“哇啊!”张二嫂高声尖叫。
银花羞红了脸。
金旺愣怔片刻,扔下木杵,拔腿就跑。
银花追出门去:“金旺,金旺哥,回来,你回来!”
金旺跑远了,没有回来。
老东家闻讯,叹息着摇了摇头。年底,叫人挑了一担米粄和油炸豆腐,连同剩余工钱,送到了金旺家。
十年后,金旺发了,娶妻生子起大屋。
乡人羡慕他行了好运。传说,他在汀江边做工时,半夜推窗看江,他看到了月光下一匹白马在江边奔跑,一闪而没。他跟踪过去,就发现了数不清的金银珠宝,他发现了古人埋下的“窖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