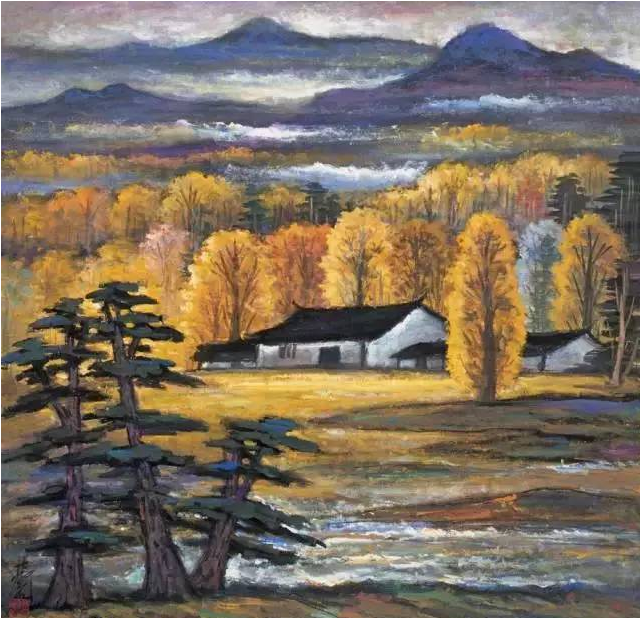【在网上看到《当代小说》2013年第12期发表的这篇评论文章,其中提及了我们《福建文学》发表的三篇小说,这三篇中,我为短篇小说《捐款记》及微型小说《A型888探测仪》责任编辑。巧的是,我在《长城》2013年第5期发表的短篇小说《纸上江湖》也引起了评论家的注意,其中说:“练建安的《纸上江湖》包裹着客家文化浓郁的神秘色彩,里面的人物也因这神秘色彩带上了某种传奇性。”谢谢评论家的鼓励,我将继续努力。】
文学如一把剃头刀
冬季主持:张丽军
文学如一把剃头刀
关建华
生活就像这片伤痕累累的大地,我们在麻木的掩盖下苟且地活着,然而文学作品却偏偏要做脱掉生活外衣的“凶手”,执着并残忍地挖掘生活的本质,讲述人生的坎坷,体验途的绝望。
“那么,脱掉它,跳一个吧。”姬中宪在小说《单人舞》(《人民文学》2013年第9期)中以这样一句话结尾,也正体现了文学撕开生活面纱的作用。《单人舞》讲述了一个极度巧合的故事,主人公准备开车去上班却发现没带车钥匙,回家取钥匙又发现家门钥匙被自己锁在车里面,更巧合的是手机也没带,还穿着一条只带一块七毛钱的睡裤。“车门和家门,互相锁住了对方的钥匙”,这是一个闭合的循环矛盾,至此,主人公踏上了寻找钥匙的途。首选想起的是存在信箱里的备用钥匙,后来才发现备用钥匙开的只是楼下大门的锁,“一把无用的钥匙,开了一把不存在的锁”。之后主人公想借电话打给准备上飞机去香港的妻子求助,可是自己没带手机,门卫的电话不能用,打公共电话钱又不够,去五金店老板娘那借电话又受了冷落。辗转多次终于借到了电话,对方是无法接通。找到开锁公司后又陷入了“有身份证才能开锁”、“开锁后我才能拿到身份证”这样的死循环。主人公在他原来以为熟悉的城市却无法找到一个能够给予帮助的人,此刻“他甚至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求助无望的时候,他决定打碎车窗取钥匙,却被破楼中抗拆迁的人误当做敌人暴打一顿,报警又被警察怠慢。主人公在一系列困窘的折磨下慢慢陷入对生活的绝望。“他想,他再也不要对这个世界如此配合了。”他手持铁管冲上破楼准备报复殴打他的人,却被设计困在了没有楼梯的六楼。如果先前是对生活的绝望并转向疯狂,此刻他的疯狂却被现实置于无处着力的失重时空。主人公想尽各种办法一层一层地向下跳,每跳一次骨折就加重一次,等再次回到熟悉的陆地,“他只剩下一条内裤”,“输得干净、彻底”。最后,主人公拖着骨折的腿爬上高架桥,走了一夜,来到“我”家,给“我”讲了整个故事。小说中涉及到破碎的爱情,冷漠的人情,虚伪的友情和尖锐紧张的政群关系,灰色调的叙述中夹着自嘲的冷幽默。最后出现的“我”只是一个虚幻的我,出现的突兀又合情合理。“我”只是代生活讲述这样一个故事,讲述主人公这一天之内的途经历。
脱掉生活外衣的还有刘照如的《果可食》(《十月》2013年第5期)。小说执着地探寻父亲当年南下掉队的原因,揭破了家人精心编织的谎言,这个谎言埋葬了痛苦的往事,支撑着贫困的生活,维护着可怜的尊严,保护着现有的爱情。当知情人都去世以后,谎言才真正梳理清楚,上一辈人所遭受的生活与内心的双重苦难才慢慢清晰,给人以长久的沉思。李铁的《送别宴》(《人民文学》2013年第9期)写的是都市小人物生存的悲哀。以送别宴上敬酒的顺序逐一引出他们与主人公赵青青之间的纠葛。送别宴上的恭维奉承与日常工作中的勾心斗角形成了巨大反差从而揭露了人际关系的虚伪。虽然赵青青最后以升迁的谎言逃离了那个压抑的工作环境,只是她的未来在哪里?这难道不又是一段途的开始。我们陷入这样一个虚伪的生活里,等待现实将残酷呈现给我们,途经多少坎坷才能看清这是一条途。李惊涛在《蝴蝶斑》(《钟山》2013年第5期)讲述了一个叫艾子女孩因长了蝴蝶斑失去了“工作”,吓跑了婚姻,最终嫁给了一个瞎子的故事。“我”少年时曾爱恋她,承诺长大后娶她,可到最后我竟然将要遗忘掉她的存在。《我们的爱情》(《十月》2013年第5期)中丈夫因不满于麻木的生活所以离婚再娶,寻求“真正”的爱情,可是他对这份新的爱情真的自信吗?文中结尾的疑问像撕去了最后的遮羞布,让生活的真实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刹那间一片寂静,无人能回答。徐则臣的《看不见的城市》(《北京文学》2013年第10期)直面生活的悲惨,描写了一对民工因打电话互不相让,发生打架致死的悲剧。解开幕后的故事,发现打与被打的人原本都是好人,只是生存的压力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还有王芸的《摩擦力》(《江南》2013年第5期)、刘宁的《啊,小寇》(《北京文学》2013年第10期)、甫跃辉的《三条命》(《江南》2013年第5期)、吴文君的《小维娜和猫》(《十月》2013年第5期)、刘乙霁的《买花》(《北京文学》2013年第10期)等都是值得一读的小说,用琐事做引,揭露公共秩序掩盖下的无序生活,展现生活道路上的艰辛与坎坷。
面对生活我们也曾反抗。葛芳的《杂花生树》(《钟山》2013年第5期)写陈欢人到中年厌恶了千篇一律的生活和庸俗的丈夫,于是她踏上寻找旧情人的旅途,在火车上却和陌生的男人发生了不应该有的暧昧情事。她清楚男人惯用的调情方式,那种方式让她恶心,却还是用酒精麻醉自己,变成一只故意上钩的鱼。陌生男人利用她发泄情欲,她也利用陌生男人寻找刺激,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欲望。陈欢只是为了逃离麻木的生活而迷茫地寻找出口,寻找旧情人也只是一个虚幻的象征,这种发泄的方式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固定本体。当天亮酒醒,无法面对放纵的昨夜,于是她放弃了对旧情人的寻找,开始又一次逃离。刘庆邦的《后来者》(《十月》2013年第5期)写了大专毕业生祝艺青在北京亲戚家的遭遇。寄人篱下,面对亲戚以“照顾”的名义进行的百般刁难,祝有口难言,最终不辞而别。可这是对生活无言的反抗吗?祝艺青最终还是没有离开北京,而是躲进了地下室的小旅馆。这条途给人无限痛苦,但因为保存幻想,我们仍不舍得离开。生活在继续,痛苦也将随生活一直继续。李为民的《指甲油》(《江南》2013年第5期)以心理医生医治心理疾患为切入点,缠绕和植入了家庭生活的琐碎,亲情的缺失、爱情婚姻的无奈和脆弱。正是由于生活的折磨,杰生才装病进行恶作剧式的反抗,只是这种发泄却伤害了无助的母亲,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发泄口。荆歌的《香如故》中千千带着对爱情的绝望杀害了大康,并用炉香掩盖尸体的腐臭。因爱生恨,扭曲了心灵,这种变态的反抗成了生活的悲剧。生活的悲剧让人发疯,可疯掉的人却又过着正常的生活。那些常理、规矩、条例束缚着正常人的脚步,反而疯狂的人却成了生活中的正常人。计文君的《卷珠帘》(《人民文学》2013年第9期)、叶弥的《独自升起》(《钟山》2013年第5期)、王秀梅《父亲的桥》(《人民文学》2013年第9期)都写了精神不正常的人,可他们的世界变得单纯,他们不用关心生活的苦难,甚至让一个正常人在一个精神病人面前“感到失败了”。非正常人过着正常的生活,这样一个逆命题让人陷入深沉的反思。这些小说无不把生活的苦难——展现给人看,或冷静、或荒诞,像是在铺一条生活的途。但这条路要指向何方,人生到底有没有希望?王大进的《爱的眼睛》(《钟山》2013年第5期)似乎给我们走下去的勇气。主人公因与妻子闹矛盾而失手杀死了她,五年牢狱生活之后重新回到小镇,一边寻找一个叫于兰的移植了妻子眼角膜的女孩,一边调查妻子当年的故事。叙述在回忆与现实的交叉中展开,如一部反复倒带的电影,对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思考,最终对往事的探索以关键人物的死亡而结束,怨恨也随之消失。在这条途中主人公承受了饥饿、贫穷、私奔、丧子、杀妻等多种痛苦,在一无所有乃至怨恨都消失的时刻,那个叫于兰的姑娘出现了,“有一只手试探着,轻轻拉住了我的手”。“过去的一切都离我远去了,然而却又有一些东西离我很近很近,近在咫尺。”残酷之后的温情文字总给人巨大的安慰,主人公在经受了痛苦磨难后,仿佛又看见了生活的希望。王彬彬曾撰文说,批评家如剃头匠;那么我说文学如一把剃头刀,呈现生活的真实原貌,但作家又非简单的呈现生活的苦难,而是在揭露真实之后再给人活下去的勇气。就像鲁引弓的《姐是大叔》(《江南》2013年第5期)里厨房亮起的灯光,戈舟《而黑夜已至》(《十月》2013年第5期)中“黎明将近”的微博,吴文君《四季调》(《十月》2013年第5期)里玻璃窗上印着的一大一小两个身影,嘉男《尘劳》(《时代》2013年第5期)之中师傅淡然安定的申请和从容的步伐,少鸿《天火》(《时代》2013年第5期)中祛瘟辟邪的艾蒿。苦难旅途的结尾都给人新的勇气,在这条途的终点,我们重拾希望,仿佛苦难已过,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我们该怎样反思精神的贫瘠
史胜英
当九月的空气中还带着酷夏的余温久久不散时,在网络中有着同样热度的“土豪”一词已成为我们的常用言语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从三十年前的暴发户、煤老板到如今的“土豪”,称谓的变化的背后,更多的折射出当今人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当物质丰厚、衣食阔绰的“豪”遇上富而不贵的“土”时,我们该怎样反思这种精神上的贫瘠?在当今文坛中,小说这一变革的风向标,总能以敏感的触觉捕捉到现实的脉动,从纷繁的世象中巧妙地将事实的内核展现给读者。
《长江文艺》2013年第9期有三篇小说是有关“风”的。风是流动的,它能吹向世间角落,它能使人清醒,它能摇撼树枝,能卷起沙尘。文学之风源自《诗经》之风,当今依旧承袭《诗经》中的土风歌谣,深入现实,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批判力度溢于纸笔。《风之步》(胡学文)中王美花为了掩盖孙女遭人猥亵的事实,忍受凶手马秃子的折磨与敲诈,面对着打抱不平的吴丁多次劝说其报案,王美花做出了极端的事情,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位饱含着爱与苦的受害人形象的农村妇女,竟然不止一次地杀害了为其伸张正义的人。她有着自己的一套逻辑,在法治精神未深入乡村的当下,法律有时无法改变或者影响世俗观念,她在请求妥协无果后只好以消极而极端的方式对现代法律作出抵抗。在农村,妇女解放的路途依旧漫长,传统的伦理道德依旧在兴风作浪,深入人们内心,法制之风到此止步不前。王美花既是受害者,亦是同谋。
《风好大》(王大进)中农民李二面对妻子抛下两个孩子而离家出走,只身来到城市寻找,最终绝望下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文中的“我”作为城市寄居者参与到小说中去,欲帮助李二,不想却一步步把李二逼向死亡。小说这种复调式的叙述是非常成功的。妻子逃离农村,不是私奔,是旅游,是对城市的向往,这种逃离是决绝的,在中国成千上万个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人中不乏如此,城市确实让生活更美好,但如此与农村极端地决裂,不免产生令人担忧的文化断层、精神断层。李二的跳楼大概是对无情的城市的对抗。正如《围城》里面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又想进去,人们一直在逃离。发表在《四川文学》2013年第9期的《躲》(陈再见)中父亲对在深圳做律师的儿子所说的,“你以为能一辈子躲在深圳吗?”躲,是对农村现实的逃避,而城市只能用来“躲”,尚无法创造和救赎,我们的根来自农村,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现实。《此案与风月无关》(李骏虎)讲述了一起城市杀人案件,而与案件相关联的每个人都有意或无意地成为了芳芳遇害的助推手。
《老费就在细水巷》(杨莉,《四川文学》2013年第9期)中老费面对烈士陵园里刻着自己名字的墓碑,想证明自己的地下党员身份和活着的现实,而政府人员却找各种理由来搪塞不予承认。峥嵘岁月,硝烟已逝,活人倒不如死人受尊重。小说所要表达的,是在对岁月的追忆中体现对人性的关怀。周志的中篇小说《忧郁的天空》(《滇池》2013年第9期)中“我”叙述着儿时的往事,如一缕潺潺的山涧溪水,在大山的云雾水气里缓缓地叙说。“我”的哥哥是榜样,是正义的化身,然而在雾气笼罩的官僚体系下寻求辨明是非、惩恶扬善的道路已变得并不理想,最后以极端的私人惩恶的方式解决,哥哥身陷囹圄,天空的忧郁无法消散。诗化小说的背后是一个沉重的现实问题。《老表》(金河村,《广西文艺》2013年第9期)则以带有都市的气息讲述了大表哥的侠义恩仇、血性宽容。《广州文艺》2013年第9期中的《逝水回波》(聂鑫森)也是一篇回忆题材的文章,在对两则小故事讲述中发现生活的善与美。黄金明的《挖洞记》运用后现代的象征方式、带有神秘色彩的叙述,渐次呈现出“洞”的象征寓意。中篇小说《狩猎者》(映川,《花城》2013年第5期)由对动物生命的漠视到对人的生命的漠视,猎走的还有人的灵魂。
发表在《滇池》2013年第9期的短篇小说《爬满铁锈的刀》(苏金鸿)讲述了一个风流成性、财大气粗的屠夫江文经与王大妹从偷情到各自离婚后结为夫妻,再到江文经秉性难改,无奈王大妹与其离婚的经历。正如王大妹所说,一个风流成性的家伙,若不改德性,约束自己,再怎么会找钱、赚钱,最终也不会有出息。记得狄德罗说过,如果道德败坏了,趣味也必然会堕落。当我们拥有了金钱,衣食无忧,如何去支配金钱却衍生出诸多问题,爬满铁锈的钢刀,爬满的更是被金钱锈住的美好的道德意识。小说以乡村为背景,以主人公屠宰户身份的设定刻画了性格爽直、豪放,带有些许水浒色彩的人物形象。此外,小说明朗的叙事节奏,利索的情节进展,都为小说增添了不少可读性与启发性。
《捐款记》(马车,《福建文学》2013年第9期)中的马鸣却是一个被村里人认为是“土豪”的穷打工者,因在一次醉酒后夸下海口,要捐钱为村里人修路,在村里人的一再追要下,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咽”,碍于面子东拼西凑了两万捐给村里。从此马鸣在村里名声大振,村人不依不饶继续要他捐款修祠堂并要去他打工的城市看他,眼看他所挖的掩饰之“坑”越来越大,已到无能填补的地步,也无法拖延、躲避,无奈地面对着窘迫的生活而不知所措。小说以捐款这一小事一方面消解了外出务工者衣锦还乡的大众记忆,另一方面反映出我们民族好面子的特征,而面子往往是拿金钱来支撑,当把面子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时,恰折射出我们的自卑和来自精神世界的贫瘠。
发表于《广州文艺》2013年第9期的中篇小说《卖脸者》(野莽)则为我们对邪不压正做了很好的诠释。兽医世家出身的何秋生一直帮扶着自幼丧父的胡春来,自然灾害时期将自己碗里难得的死猪肉让给胡吃,文革结束后又将宝贵的上大学的名额无私地给了胡春来,何秋生没想过要回报,可胡春来学成归来后不仅知恩不报,更是变本加厉地一步步将何秋生逼出兽医站,下岗后的何秋生只好去拍卖自己的大脸。小说若到此结束便是一个悲剧了,然而作者一转笔使主人公绝处逢生:一位香港商人听说了何的故事,以高价拍下他的脸,并用拍下的资金买下兽医站,还让何当上站长。
相而似之,作家以细微的视角展现个体生命在当下的精神状态的还有许多篇。发表在《四川文学》2013年第9期的小小说《慧芳的月亮》(陶群力)描述了善良的农村女孩慧芳辍学、嫁人、进城打工、遭弃等一系列不幸的经历,但一轮皎皎的明月升起,在黑暗的夜里,一丝光亮,便仍有希望。发表在《花城》2013年第5期的两篇短篇小说《割礼》(田耳)与《桠杈打兔》(晓苏)表现了农村带着淳朴的情与爱。《割礼》中小夫妻就计生结扎一事上演了一出《麦琪的礼物》,读来给人一种带有山枣酸楚的甜蜜与温馨。《桠杈打兔》则讲述了一位以“桠杈打兔”为口头禅的毛洞生不如意的一生,好运总是在唾手可得之际飞走,忠厚、勤快的他哭过、恼过,最后归于平静,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着自己的幸运:未遭不幸便是最大的幸运。第9期《广州文艺》中的另一篇小说《乡村轶事(邵一飞)唱了一曲明快的乡村小调:村主任马领借开会之机在广州大吃大喝,医生张驼子借看病之机给了他一顿教训。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用了许多西南方言和谚语,展现了独特的地方乡土风情。
乡土这块人类灵魂的栖息地,滋灌着人类精神的麦田,无论城乡,无所谓贫富。因为金钱是永远无法赎买这片宝贵田地的。
《玫瑰效应》(林筱聆,《福建文学》2013年第9期)与《春暖花开》(第代着冬,《滇池》2013年第9期)都讲述了因一束玫瑰和情书引发的猜忌与误会,牵扯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同样在《福建文学》2013年第9期,《A型888探测仪》(凌鼎年)以接反了的探测仪表现人心难测,人不经意便会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三野家族》中从野猪窝闯出,辛苦供儿子上学,上的却是野鸡大学,梦的幻灭体现的是现代社会构筑的脆弱。杨遥的《给飞机涂上颜色》,颜料是正义,是美好善良的本质精神,当飞机飞不动的时候,只有颜色与飞机相伴,人就是一架飞机。《康东的去向》(徯晗)中康东如范进一样渴望通过写作寻求成名,最终被写作毁掉,体现现代人被功名缠身的悲哀。
此外,小说里的爱情婚姻是永远表现不完的题材。《梁子的婚事》(杨牧原,《四川文学》2013年第9期)从梁子相亲到结婚,体现了对现代婚姻的焦虑。《庭院》(《广州文艺》2013年第9期)是对中年离婚女人内心“庭院”的观照,那荒芜的庭院要开始收拾了,没有男人的倚靠依然要生活得潇洒。《广州文艺》中的另一篇小说《把你的手给我》,温情的故事给爱做了很好的注解。
我们每个人应当成为精神世界里麦田里的守望者,作家更有责任守望人类精神的麦田。正如《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所说的,“我就站在这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一个跑向悬崖的孩子”。
生命之花幽然开放
何泓阳
人们常将花儿比作女子,这些女子中,有的娇艳如玫瑰,有的纯真如雏菊,有的高洁如玉兰,也有的怒放如牡丹。她们渴望幸福,因此痴情不已。皆因痴情,她们迎来了不同的命运,属于自己的生命之花也在静处幽然开放。
刊登在《飞天》2013年9月号言子的短篇小说《李花飞》营构了一个难得的、纷繁尘世之外的清静空间,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将女性独有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故事的地点发生在远离俗世喧嚣的真武山,讲述了一个向往爱情的人找不到爱情的故事。主人公李花“一生为情所困”,离异两次却始终没有放弃寻找爱情的希望,她所期待的爱情“不仅仅是一个男人、一段婚姻,一场性,”现实中,李花与女友游山而偶遇居士,居士疏朗俊逸,平静中带有几分飘逸,气度不凡,这使李花暗暗萌生了爱恋。因无法表达自己的倾慕之情,李花住进了真武山,也成了一名居士,或远或近地将目光游离在居士身上,在花开花谢中等待居士的归来。梦境中,这位身着玄色衣衫的男人在山林之间披荆斩棘,以一位开拓者的形象将李花深深吸引住。李花默默观察着居士,而居士却在朝阳初现时,变成白鸟向晨曦飞去。后来的梦境里在“山风摇响松涛”之际,残花纷纷凋谢之时,“花跟随凋谢的李子花,滑落地上”,留给读者无尽的想象,颇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李花将梦境融入现实中,更使自己久久地沉醉在梦境中。整篇小说交织在梦幻与真实之间,语言纯净简洁,气氛宁静悠远而不失浪漫。小说由梦开始,以梦结束,想象奇特,超然脱俗。
同样刊登在《飞天》2013年9月号樊建军的中篇小说《有花出售》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将女性拯救与自我拯救的心灵历程细致精微地展现出来。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谢静面对家庭的变故用尽浑身解数对家人进行拯救与自我拯救的过程。义宁州城的人们因谢老头家的三只凤凰而将目光久久地聚焦在十八间,欲望、谩骂、诅咒、忌恨相互交织。谢静自始至终都洁白得像朵白菊,大姐谢青因在高中时遭遇强奸而只身去了南方,从此杳无音信,二姐为了男人拼命减肥,即使面对瘫痪的父亲也无动于衷。为维持生计,谢静先后开了水煮店、美人坊,最终不得不到阳光宾馆工作。这一切看似平淡,背后隐约却有一双无情的大手掌控着。谢青的突然归来让花街再次沸腾起来,身心俱疲的谢青只想找到归宿,目光却偏偏落在了混混儿西皮身上,最终无法忍受西皮的家暴与羞辱将其杀害。二姐谢筝患上厌食症离开人世后,谢老头也带着遗憾撒手人寰。疲惫不堪的谢青一直处在拯救的位置,她竭尽全力想阻止悲剧的发生,却发现命运是如此的难以把控,她无时无刻都在渴望找到一个坚实的臂膀实现自我拯救,现实却将她的幻想无情地重重击碎。小说的结局如静场般沉重,让人回味良久。
《时代文学》2013年9月(上)刊登的郝炜华的《老宅》以阴郁的笔调讲述了发生在老宅周围的故事。小说营造了一个底层社会的空间,离婚的男人、基督徒、强迫症患者、暗娼、夜宵摊营业者、住在窝棚里的老男人等等看似互不协调却又形同整体地生活在老住宅区中。在这几乎让人窒息的混乱中隐隐暗藏着一种随时会发生大事的危机感,然而在这不协调中老宅居民微细而又珍贵的相互同情与关心终究没让人彻底绝望,小说的主人公便是家里白得出奇的夜宵摊营业者刘兰花。作为带着痴呆女儿入住老宅的弱者,刘兰花因奋不顾身地维护老宅的利益而获得了老宅居民的认可与帮助。刘兰花对肮脏、患有精神病的窝棚老男人的关心更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窝棚失火后,刘兰花竟将老男人接进了自己的家,连信奉基督教,讲求行善为先的“我”的父母都惊叹不已。然而,刘兰花对接回家中老男人的恶语相对与打骂使小说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从她充满迷惑性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得知老男人应该是她的亲人。此时,刘兰花的无私与自私、在众人面前的和善与对待老人的凶残之间的对立猛烈地撞击着读者的心,小说的张力得以扩张。小说在最后迎来了老宅的拆迁,但愿那些“隐藏在生活表象下的、无法向人言说的、给人造成无尽伤害的幽暗、肮脏之事会随之一起被拆迁、被摧毁、被埋葬”,可是被摧毁、被埋葬了就永远不存在了吗?小说的结尾引人深思。
《北方文学》2013年9月(上)刊登了毛芦芦的短篇小说《苍屋桐花》,小说运用闪回的手法将现实与桐花的回忆完美地穿插起来,在凄美淡然的文字表象下,渐渐浮上水面的真象令人触目惊心,读后心情无法平静。天真烂漫的桐花姐妹因母亲离世被桐屋娜接到桐屋抚养,这善良的背后却隐藏着桐屋那重重的心机。比桐花大十三岁的秋明树的到来引发了桐屋娜对桐花深藏不露的嫉妒。故事的第一次高潮发生在桐屋娜欺骗整个心思扑在秋明身上的桐花,将她嫁给了自己的儿子三强,可谓一箭双雕,殊不知这一举动造成了三个人命运的转折。秋明的出走,桐花儿子的意外死亡使桐花患上了心痛病。秋明的再次归来也预示着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爆发。表面上妥协的桐屋娜在两人沉浸在爱情的欲火中时扔出了一颗能震碎心脏的“炸弹”——将一个与桐花去世的孩子一模一样活动木头人扔进了两人偷欢的窗口,从此,桐花内心最敏感的一条神经被木头孩子彻底拨乱,精神彻底崩溃,小说因此迎来了第二次高潮。
痴花半壁,每朵花有每朵花的命运,无论平凡高贵,惟有精心栽培,生命之花才能长久绽放。《时代文学》2013年9月(上)刊登的魏留勤的《丛树根寻妻记》以尖锐犀利的笔调写出了城市文明对人的异化而导致的一个家庭的破裂,直面现实,发人深思。张映勤的《小街人物二题》以远距离遥望的姿态讲述了特殊年代外人眼中马丽雅的命运沉浮,视角独特,引发人们的好奇心。《长城》2013年第5期刊登的白天光的《赤芍地》故事性极强,用干净洒脱的语言娓娓道出了赤芍地传奇女人的故事。而姜燕鸣的《白雾》将女性对感情的依赖淋漓尽致地写了出来,其中暗含了命运的无常。小说中既有不能见光的肮脏,有生命的颓败,也有生命的觉醒。练建安的《纸上江湖》包裹着客家文化浓郁的神秘色彩,里面的人物也因这神秘色彩带上了某种传奇性。《飞天》2013年9月号马悦的《阿尤旦》中阿西耶是母亲,又是妻子和儿媳,她纯洁、善良、刚毅的品质不免令人对她的悲惨遭遇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与敬意。
《北方文学》2013年9月(上)刊登的谭岩的《破灭》讲述了所有人希望的破灭,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小说。农村来的江春丽进入城市后费尽心机希望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最终却被人利用惨遭抛弃,小说最后虽写她良心发现,但所有希望破灭后所造成的精神、肉体伤害将无法偿还。周月霞的《赖四媳妇》描述了一个没有自己名字的女人的突然离世,小说用轻松的语言还原了女人善良、淳朴的生命本性,最后两个孩子的悲天恸哭才是小说的高潮。白勺的《春天的隐痛》线索明晰,将主人公工作与生活的冲突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姑姑的身世之谜在矛盾中也渐渐隐现。陆荣斌的《躲藏起来的扑克》写出了叶丽秀为让丈夫戒赌而做出的滑稽、荒诞行为。《山西文学》2013年第9期发表了房光的《珍珠婚》,用写实的手法写出了“我”父母的30年的婚姻,其中的摩擦碰撞与近乎彻底的隔阂需要父母双方共同的努力才能化解。同样是房光的《入冬记》从侧面展现了农村女人对于生活的知足,故事真实而富有情趣。
《鸭绿江》2013年第9期杨红的《二十厘米》诠释了中年危机所带来的心灵的寂寞,二十厘米是一个空间距离,更是一个心灵距离,直面了理想与现实、梦幻与真实的差距。徐东的《见面》以两个陌生人打电话的方式来彻底地暴露了自己的内心,袒露了自己的情欲,形式独特,结局却令人出其不意。朱宏梅的《末春》以细丽的笔致展现了战争背景下的生死离别与生存的挣扎,在此之下的少女懵懂的爱情也变成了奢侈之品。《山东文学》2013年第9期(上)发表的郑建华的《叉子的活儿》讲述了女人的命运便是与丈夫叉子的活儿的运气的赌博,但她对此却心甘情愿,在肮脏与血腥背后保存了一丝温情。张明亮的《一人一个诨名字》则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生命最原始状态的粗野。韩松礼的《红盖头》在大喜与大悲中写出了丑媳妇的不幸遭遇,她所体现出来的担当与自尊更加令人同情。《芒种》2013年第9期(上)徐虹的《暮色》相似于杨红的《二十厘米》,以阴冷的笔调道出了中年危机来临时人们所经受的精神折磨。《第二十一店》则写出了女人想象中的心灵争斗,里面充斥着敏感与尊严,更不乏岁月沉淀下来的那份安静。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